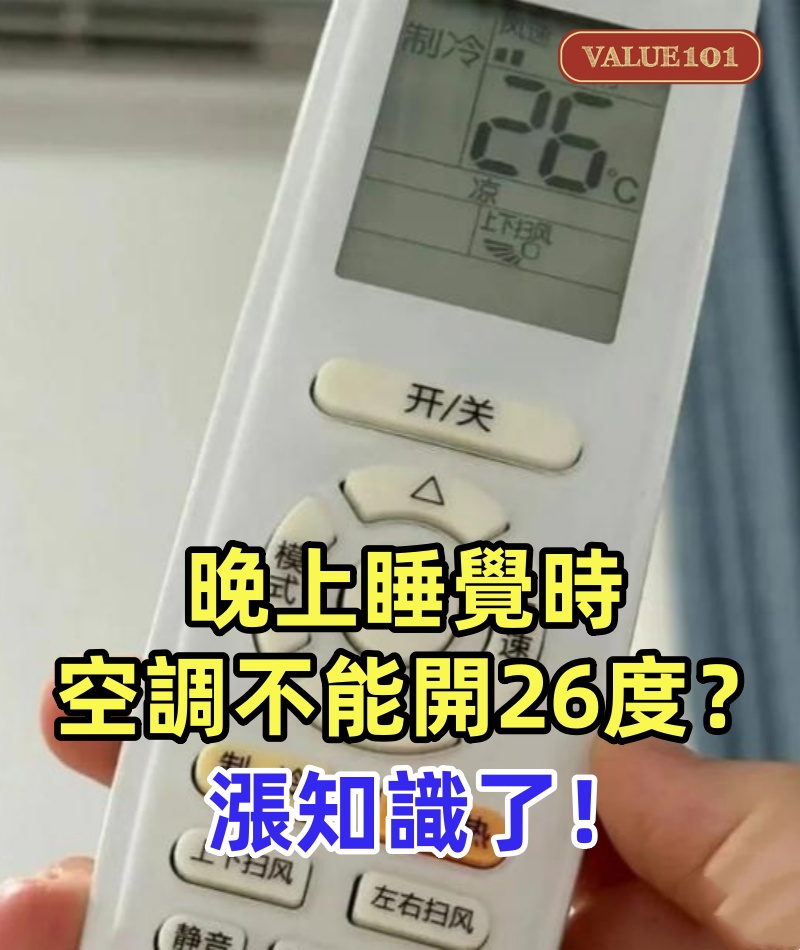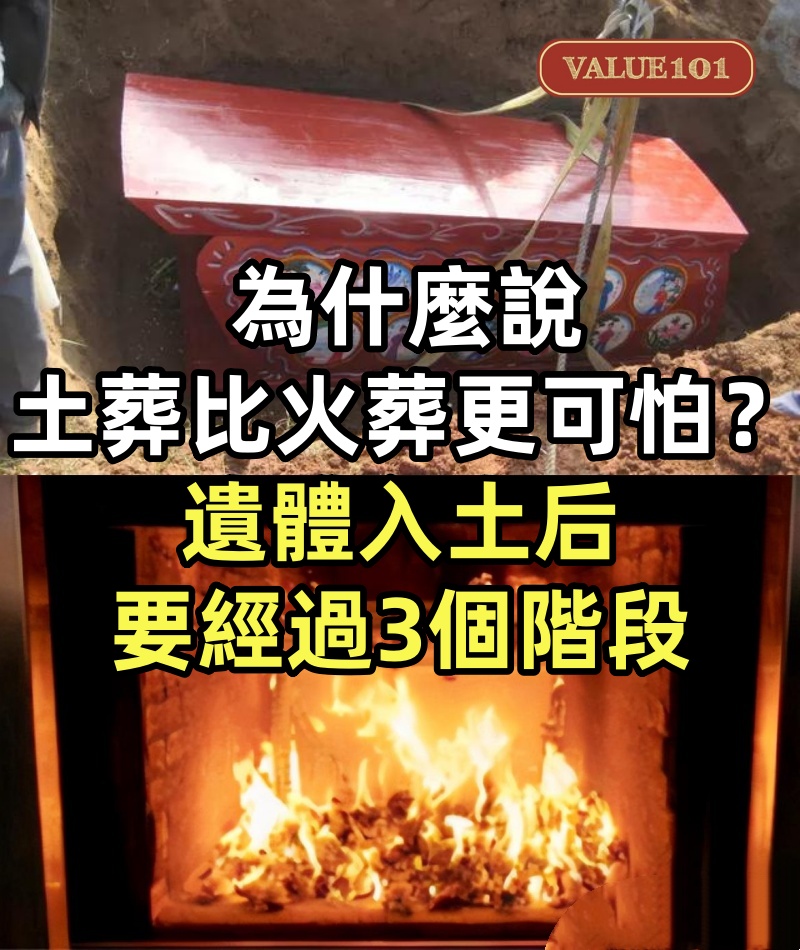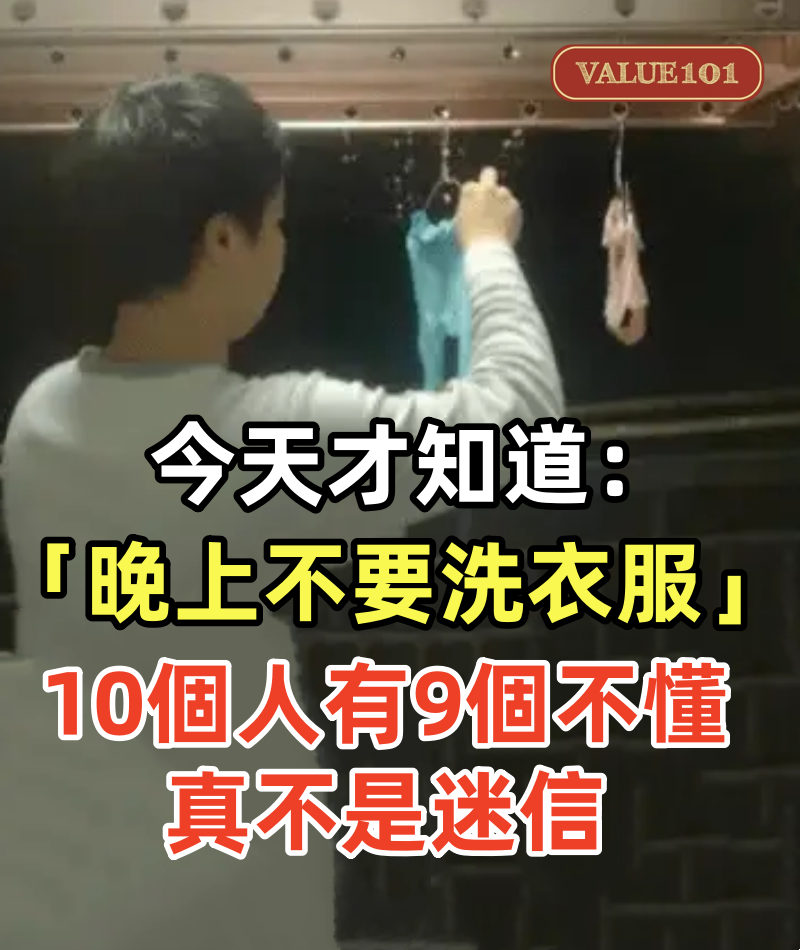女子嫁到非洲16年沒回家,母親退休去看望,見到女婿后愣在原地


你女兒不是嫁去非洲了嗎?
十六年啦,年年都說要回家,年年都不見個人影兒。
」
在小區門口的水果攤前,幾個熟人一邊挑著橘子,一邊交頭接耳地議論著。
雖說聲音不算大,可卻清清楚楚地傳進了董雅麗的耳朵里。
董雅麗沒有回頭,也沒有吭聲,只是低著頭,手指有一搭沒一搭地摩挲著口袋裡的小紙片。
那是她早晨剛翻出來的信封,最上角貼著一枚已經褪色的非洲郵票。
她心裡清楚,大家議論的就是她的事兒。
她的女兒孫穎,16年前遠嫁到了東非的一個國家,從那以後就再也沒回過家。

甚至連視頻都沒打過,每年就只有在春節前寄來一封信,信里還夾著一兩張照片,信上總是寫著一切都很好,丈夫對她很好,生活雖然簡單,但很安穩。
「媽,非洲的太陽可大了,我的皮膚都晒黑了,你別擔心我。
」
「媽,你退休了嗎?
要多注意身體啊。
」
「等我有空了,一定回來看你。
」
可這一等,就是整整十六年。
董雅麗年輕的時候是初中語文老師,習慣了過那種細碎嚴謹的日子。
她原本以為,女兒就算嫁得再遠,那也只是暫時的。
可十六年過去了,她從五十多歲熬到了滿頭白髮,等來的只有一封封簡短的信。
那時候她還在上班,常常安慰自己:「孩子工作忙,忙。
」
後來退休了,她開始每天眼巴巴地盯著信箱,盯著路口,盯著那扇熟悉卻又越來越空蕩的大門。
她不止一次地想給女兒打個電話,可每次撥過去,非洲那頭總是信號不好。
每次孫穎打來電話,就只說一句話:「媽,我挺好的。
」語氣輕快得很,就好像生怕多說一秒就會露出破綻。
董雅麗不是沒起過疑心,可又怕問得太多,把那點僅存的聯繫都給弄沒了。
直到那天晚上,她做了個夢。
夢裡,女兒穿著白裙子站在一片乾裂的土地上,四周漆黑一片,女兒不停地喊著:「媽,你別信我寫的那些話,媽,我想回家……」她一下子被嚇醒了,坐起身來,發現枕頭都濕了一片。
這一次,她沒再像往常一樣等著信來,而是拿起紙筆,給女兒寫了一封親筆信。
信里沒有責怪,也沒有質問,就只寫了一句話:「我想去看看你,可以嗎?」三周后,她收到了回信。
信紙還是那熟悉的牛皮紙,字跡依舊整齊:「媽,你真要來嗎?
我……我挺感動的。
我們這邊條件不好,但你放心,我會準備好一切的。
等你到了,我來接你。
」信末的落款還是「孫穎」。
她把這封信反覆讀了三遍,總覺得信里那句「我挺感動的」,好像藏著什麼話沒說完。
當天下午,她就去了街道辦事處辦理護照和簽證。
她可不是一時衝動,只是突然明白了一件事……要是再這麼等下去,她可能永遠都不知道,孫穎到底過得是不是真的「挺好」。
街道辦出入境窗口是個年輕小伙,看到她填的目的地時,愣了一下:「您是要去……這裡?」他指著表格上那一串拗口的東非地名,語氣裡帶著一絲懷疑。
「我女兒嫁那邊了,我要去看她。
」
小夥子抬頭看了她一眼,欲言又止,最後還是點了點頭:「那邊情況比較特殊,可能要提供一些額外的材料。
您有沒有她的身份證明,或者邀請函?」
「她每年都寄照片和信回來,我都留著呢,有幾封信里還寫了具體地址,還有她丈夫的名字。
」
「那您先把這些交上來,我幫您錄入申請系統。
」第二天,董雅麗把所有的信件都裝進了一個透明文件袋帶了過來。
還有一張照片,是孫穎和她兒子拍的……混血男孩皮膚偏黑,笑容很開朗,可照片里那個男人始終沒有正臉。
「您女婿有沒有正面照片?」小夥子忽然問道。
董雅麗愣了一下:「她說他不喜歡照相,也不太會說中文。
」小夥子「哦」了一聲,又低頭敲鍵盤,嘴裡不經意間小聲嘟囔了一句:「好像是那邊某個……什麼家族……」
董雅麗沒太聽清,就問他:「你說什麼?」 「沒事,就是那一帶部落比較封閉,我們有時候也得核查一下安全情況。
」
她沒再追問,可從辦事大廳出來的時候,心裡卻多了一絲說不出的異樣。
那天晚上,她坐在沙發上,一邊擦著藥瓶,一邊看著桌上的信紙發獃。
茶几上擺著女兒十幾年來寄回來的照片,一張張地鋪開。
她忽然意識到……所有的照片里,孫穎都是一個人,或者牽著孩子,從來沒有一張有她丈夫的照片。
她開始想象那個「非洲女婿」的模樣。
是不是很高大?
是不是很善良?
是不是像孫穎信里說的那樣「體貼」?
還是……根本就不是那麼回事兒?
第二天清晨,她翻出了家裡多年的老拉杆箱,把它擦得鋥亮,然後把衣物、藥品、證件一樣一樣地裝進去。
臨走前,她從抽屜最底層取出了一張孫穎大學畢業的照片,放在了貼身口袋裡。
那是她最後一次看到孫穎「像中國人」的樣子。
照片里,孫穎穿著藍白相間的學士服,站在南京大學校園裡,笑得那麼意氣風發。
她的女兒,本來可以有好多條路可以走的。
董雅麗心想:哪怕只是為了看她一眼,我也該去了。
飛往東非的航班是在凌晨起飛的。
董雅麗坐在靠窗的位置,手裡緊緊地捏著護照,目光透過小小的舷窗,看著機場夜色沉沉,燈光就像豆子一樣稀疏,眼神里滿是難以言說的複雜情緒。
她從來沒想過,有一天自己會出國,更沒想到,是為了去進行一次遲到了十六年的「探親」。
飛機起飛的時候,她的心就像被拎起來一樣懸著……既忐忑,又激動,還有一絲沉重的預感。
近20個小時的旅程,一路顛簸。
她幾乎沒怎麼睡,耳邊充斥著飛機的轟鳴聲和各種陌生語言的交談聲。
落地的時候,耳膜刺痛得厲害,但她顧不上這些,只想趕快見到孫穎。
抵達機場的時候,是當地時間下午三點。
董雅麗拎著行李箱走出航站樓,撲面而來的熱浪讓她一時間有些暈眩。
空氣中瀰漫著塵土和焦炭混合的味道,遠處是一排排簡陋的棚屋,還有一些舉著長槍的安保人員站在入口附近。
她從來沒見過這樣的場景。
手機幾乎沒有信號。
她站在機場門口,四處張望著,尋找那張思念了十六年的臉。
「媽!」
人群中傳來一聲中文呼喊,她猛地回過頭。
孫穎站在不遠處,穿著一身略顯舊色的長裙,頭髮被烈日晒得乾枯發黃,膚色比過去黑了整整三度,可那笑容,還是她記憶中女兒的模樣。
「小穎!」董雅麗幾乎是顫抖著走上前,一把抱住了她。
那一刻,她有無數的話想說,可一句也說不出來。
眼淚在眼眶裡打轉,手卻緊緊地拉著孫穎的手臂,就好像怕她再一次消失。
孫穎聲音發顫:「媽,你瘦了。
」
「你也瘦了。
」董雅麗哽咽著說道。
她看著女兒的臉,那是一張既熟悉又陌生的容顏。
比照片里還要黑、還要瘦,可眼神里多了些她從未見過的東西……一絲疲憊?
還是某種防備?
她不確定。

飯後,天色暗了下來。
夜幕在這片乾熱的土地上落得比國內更快些。
天空是一整片深藍色,沒有高樓的阻擋,星星密密麻麻的,亮得就像掛在眼皮上一樣。
董雅麗站在院子門口,微微踮著腳,望著那條泥土路的盡頭,視線卻穿不過遠處的黑暗。
那條路白天看的時候只是塵土飛揚,現在卻像一條沉默的蛇,蜿蜒著蜷伏在夜色中,死寂無聲。
院子很安靜,只有牆角一隻貓頭鷹低低地叫了一聲,驚起了一群不知名的夜鳥,撲稜稜地從灌木叢中飛起,又迅速沉入了更深的黑暗裡。
屋裡,孫穎在廚房燒水,她的動作很輕,卻掩蓋不住灶膛里的噼啪聲。
她低著頭,表情平靜,可手指卻無意識地一遍遍擦著鍋邊的焦漬,就好像在借著這個動作讓自己鎮定下來。
董雅麗站了很久,終於回頭走回屋裡,拉了張小藤椅坐下。
「媽,你累了吧?」孫穎遞來一杯溫水,語氣溫和。
董雅麗接過杯子,輕輕啜了一口。
水裡帶著淡淡的煙火氣,就像是灶台熬出來的,還夾雜著泥土的味道。
「這邊水質還行嗎?」她順口問了一句。
「燒過就沒問題。
」
董雅麗點點頭,把杯子放在腿上,停頓了一下,又緩緩問道:「你丈夫……他今天,真的不回來了嗎?」
孫穎低頭掖了掖圍裙下擺,神情略微有些尷尬:「他說今天村裡有個長老葬禮,比較重要。
」
「他是什麼身份?」董雅麗頓了一下,「怎麼我來了,他都不露面?」
孫穎輕聲說:「他在部落里地位挺高的,很多事務都要處理,他不喜歡陌生人。
」
「我不是陌生人。
」董雅麗抬頭看著她,語氣不重,但字字都很清晰。